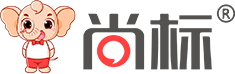徐琳:商標圖樣的著作權保護之困境與出路
來源:《電子知識產權》2014年第11期 發布時間:2016-08-18 10:00:00 瀏覽:1762
《商標法》保護在先著作權條款的立法精神和審理標準探析 摘要:《商標法》中“申請商標注冊不得損害他人現有的在先權利”條款的立法目的并非要解決“權利沖突”,而是以保護他人其他合法在先權利為出發點,規制有違誠實信用原則的不當商標注冊行為。在適用本條款對在先著作權進行保護時,應回歸到“著作權保護”本身去確定證明標準,不應對“獨創性”提出較高要求。同時,在法律適用中應體現維護誠實信用原則、遏制惡意搶注的立法精神,合理分配雙方當事人之間有關作品著作權權屬的舉證責任。
關鍵詞:在先著作權 商標圖樣 作品獨創性 著作權權屬 實質性相似 接觸可能
《商標法》第三十二條規定:“申請商標注冊不得損害他人現有的在先權利”。本條款中的“在先權利”是指除商標權以外的其他合法在先權利,其中包括在先著作權。《商標法》下在先著作權獲得保護的前提有三:一是系爭商標與他人在先享有著作權的作品相同或者實質性相似;二是系爭商標注冊申請人接觸過或者有可能接觸到他人享有著作權的作品;三是系爭商標注冊申請人未經著作權人的許可。
實踐中存在大量在先商標注冊人依據在先注冊商標中的商標圖樣主張在先著 作權的案件,對此類案件中“商標圖樣”是否構成“作品”、作品創作時間、著作權權屬、在先商標注冊證和著作權登記證書的證明效力的認定以及雙方當事人舉證責任的分配等方面頗有爭議。本文擬在探求《商標法》對在先著作權保護的立法精神的基礎上,圍繞在先著作權保護的審理標準,就“作品”獨創性的要求,“實質性相似”、在先著作權權屬以及“接觸可能”的判定進行分析。
一、“申請商標注冊不得損害他人現有的在先權利”條款的立法目的
對于《商標法》中“申請商標注冊不得損害他人現有的在先權利”規定的立法目的,通說認為是解決在后商標權與其他在先權利之間的沖突。欲析清本條款的立法目的,必須先闡明何為“權利沖突”?同一權利客體上同時存在兩個以上的合法權利,且該不同的權利分屬不同權利主體,是權利沖突產生的前提;當因權利邊界存在不確定性、模糊性,或者一方權利主體濫用權利,導致一個權利主體行使其權利會構成對他人權利的限制或損害時,權利沖突就實際發生。解決權利沖突的方法一般是通過立法,劃清權利行使的邊界,或者通過對權利進行限制,實現不同主體間的利益平衡。例如,我國2013年《商標法》第五十九條關于商標在先使用權抗辯的規定,就體現了解決權利沖突,限制商標權利濫用的立法精神。權利沖突應該是合法的、正當的權利之間所發生的沖突,而解決權利沖突的手段是劃清界限,或通過權利限制實現不同權利主體間的利益平衡。
由此可見,“解決權利沖突”對本條款而言其實是一個偽命題。以在先著作權為例,若商標注冊申請人是在接觸過或者有可能接觸到他人享有著作權的作品的情況下,仍然未經著作權人許可,將與他人享有著作權的作品相同或構成實質性相似的標識申請注冊為商標,其注冊行為從性質上就是有違誠實信用原則的不當注冊行為,即該“商標權”的取得具有不正當性。此時,并不存在合法的商標權與合法的著作權之間的“權利沖突”,而是不當商標注冊行為與他人合法在先著作權之間的“沖突”。對該“沖突”的解決也并非是通過權利限制,而是對在后不當注冊的商標不予核準注冊或者宣告無效。同理,若他人在后的商標注冊并未損害他人在先的著作權,如主張在先著作權的標志與該商標圖樣并未構成實質性相似,或不能證明存在“接觸可能”,則在后的合法商標權與在先的合法著作權之間亦并未產生“權利沖突”。
因此,本條款的立法目的并非要解決“權利沖突”,而是以保護他人其他合法在先權利為出發點,規制有違誠實信用原則的不當商標注冊行為。正確理解本條款的立法目的,對于在《商標法》下對在先著作權進行有效保護具有重要意義。
依據《伯爾尼公約》,任何一成員國公民的作者,或者在任何一成員國首次發表其作品的作者,其作品在其他成員國均應自動受到保護,因此,與商標權保護不同,著作權保護在公約成員國之間是不存在地域限制的。而且,與普通商標權保護以“相同或類似商品上”為限不同,若某在先創作的作品被他人未經許可注冊為商標,則其權利人可依據在先著作權請求該商標不予注冊或無效宣告,而勿論其注冊在何種商品上。基于此,有觀點認為,適用本條款時應對“作品”的獨創性要求、在先著作權的舉證實行嚴格的證明標準,否則這種不考慮實際使用商品類別的保護,會使得標識構成作品的在先商標獲得超越馳名商標的保護程度,對某一商標標識形成壟斷,破壞了商標注冊及制度體系。實踐中,持上述觀點的人不在少數。
本文認為,上述觀點曲解了《商標法》規定“申請商標注冊不得損害他人現有的在先權利”的立法本意。如前所述,本條款的立法目的是以保護他人其他合法在先權利為出發點,規制有違誠實信用原則的不當商標注冊行為。因此,若他人在先著作權可能會因第三人的不當商標注冊行為而受到損害,其就有權依據在先著作權請求該商標不予注冊或無效宣告,不能因某構成“作品”的標識被注冊為商標,就剝奪或者限制其尋求著作權保護的權利。況且,著作權保護與商標權保護是兩種不同的法律關系,前者以保護智力創作成果為原則,后者以禁止混淆為原則;前者以兩圖樣構成“實質性相似”為前提,而后者中的商標圖樣可以“相同”,也可以“近似”。馳名商標可以獲得跨類保護,此時在后的商標圖樣只需與其近似即可,而且引證商標的知名越高對商標近似判定也會越嚴格。但是對于在先著作權保護,則必須以商標圖樣與他人在先作品構成“實質性相似”為前提。因此,不能簡單地得出圖樣能夠獲得著作權保護的商標會獲得較之馳名商標更高的保護標準或保護機會的結論。
綜上,在適用本條款對在先著作權進行保護時,應回歸到“著作權保護”本身去確定證明標準,而不應強調“商標特色”,從“維護商標注冊制度”角度出發提高證明標準;同時,在法律適用中應體現維護誠實信用原則、遏制惡意搶注的立法精神,有效制止損害他人在先著作權的不當商標注冊行為。
二、“作品”與“實質性相似”的判定
在先著作權成立的基本前提是主張著作權的圖樣構成《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品”。《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二條規定:“著作權法所稱作品,是指文學、藝術和科學領域內具有獨創性并能以某種有形形式復制的智力成果。”根據該規定,作品需要同時具備獨創性和可復制性,表現形式可以為文字、音樂、美術、電影、建筑、攝影等。如何理解作品“獨創性”的要求,是判定某標識是否構成作品的關鍵。對此,實踐中主要存在兩種觀點:一種觀點側重于從“原創性”、“初創性”的角度來解讀“獨創性”,強調“一件作品的完成應該是作者自己的選擇、取舍、安排、設計、綜合、描述的結果”[1],“獨創性與作品的文學、藝術或者科學價值無關”[2],“不應對獨創性提出高要求,只要具有稍許的個性、創造性,作品中體現出了作者哪怕是微小的取舍、選擇、安排、設計,就應認為具有獨創性”[3]。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獨創”應該包括“獨”與“創”,其中,“獨”是指獨立創作完成,而“創”是指作品應達到一定的智力創作高度。例如:在最高人民法院(2012)知行字第38號行政裁定書中就明確表達了這種觀點,認為:“《著作權法》保護的是具有獨創性的作品,必須同時符合‘獨立創作’與‘具有最低限度創造性’兩個方面的條件才可能成為《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品。受《著作權法》保護的作品不僅要求獨立完成,還需達到一定水準的智力創造高度,智力創造性能夠體現作者獨特的智力判定與選擇、展現作者的個性并達到一定創作高度要求,‘獨’與‘創’缺一不可”,并據此判定系爭商標標識(見圖一)與“超羣”二字普通篆體及隸屬的不同書寫方式比對,其表現形式并未顯示存在獨特的風格,僅存在細微的差別,該標識未達到一定創作高度,不具有獨創性。正是因為實踐中對“獨創性”標準的判定存在一定分歧,導致在“作品”的判定上出現許多標準不一的行政裁定與司法判決。例如,在若干商標行政裁定和司法判決中,認定了某些構圖設計較為簡單的圖樣(見圖二、圖三、圖四)構成“作品”,而某些商標圖樣(見圖五、圖六、圖七)則因組成要素或構圖過于簡單而被判定缺乏獨創性,不構成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品”。
《著作權法》對著作權進行保護的立法目的從本質上說是以保護著作權為依托,鼓勵社會公眾的創作熱情,實現促進知識傳播與創新、推動人類社會文化發展繁榮的終極目標。依據該立法目的,為了鼓勵社會公眾的創作熱情,不應以某作品的文學、藝術或者科學價值高低來作為其能否獲得著作權保護的前提,只要其是獨立完成,通過線條、色彩或者其他方式產生了一定的審美意義,體現了作者獨特的表達和為此投入的智力勞動,就可以判定為構成《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品”,應獲得著作權的保護。尤其對于商標圖樣來說,有時簡約、醒目的設計相對于繁復的圖樣更具有識別上的優勢。因此,對于商標圖樣是否構成作品,不能僅以其“圖樣表現形式簡單”或者“創作高度不夠”而予以否定;也不能因為某圖樣是作為商標圖樣設計,而非旨在公開發表的“作品”,就否定其創作者在設計過程中投入的智力勞動。例如常見的耐克、阿迪達斯、李寧公司的圖形商標圖樣(見圖八、圖九、圖十),包括上圖五所示安踏公司的圖形商標圖樣,其表現形式雖然簡單,但是卻凝聚了設計者獨具匠心的創作,其付出的智力勞動也絕非完成一幅簡單的圖畫所能相提并論的。若僅以圖樣構成簡單,創作高度不夠為由否定其構成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品,則完全背離了著作權法鼓勵創作,保護創作者智力成果的初衷。
只是,與商標的知名度程度不同,其獲得保護的范圍也不相同一樣,作品的創作高度不同,其權利范圍也有所差別。應充分運用“實質性相似”這一要件對作品的保護范圍進行確定,而不應簡單否定表現形式較為簡單的圖樣可以構成作品,排除其獲得著作權保護的可能性。對于表現形式較為簡單的作品,對實質性相似的判定要求較之構圖較為完整的美術作品,應更為嚴格。只有兩圖樣在線條設計或色彩、構圖上相同或者幾乎完全一致,抄襲明顯的情況下,才能獲得著作權的保護。
因此,與生效裁定及判決觀點不同,本文認為,在第4445480號“DKK”(見圖十一)商標異議復審案[4]中,雖然主張在先著作權的圖樣(見圖十二)構圖較為簡單,僅是對英文字母“DDK”進行了一定的變體設計,但是,該設計能夠體現其作者從增加標識美感的角度出發,對英文字母“DDK”的表現形式進行了選擇、安排、設計,這體現了作者的獨特的表達和為此投入的智力勞動,應判定該圖樣構成《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品。只是,因其表現形式較為簡單,對“實質性相似”的判定應以被異議商標圖樣與之相同或幾乎完全相同為標準。被異議商標為常見字體的英文字母組合,與在線條設計、表現形式等方面存在差異,二者未構成“實質性相似”,據此判定被異議商標未構成對他人在先著作權的損害,而不應以未達到作品的“創作高度”而判定不予進行在先著作權的保護。
同樣,在第3950331號圖形(見圖十三)商標異議復審案[5]中,主張在先著作權保護的商標圖樣(見圖五)雖然較為簡單,但是具有一定的設計性,通過線條的構成形成了的藝術美感,應視為構成作品,不應以該圖樣未達到作品的創作高度為由判定不予進行在先著作權保護。而是應以該圖樣與被異議商標的圖樣在線條、構圖要素設計等方面均存在一定差異,未構成“實質性相似”為由判定被異議商標并未損害他人在先著作權。
綜上,應從“原創性”的角度上理解《著作權法實施條例》中的“獨創性”要求,不應對“獨創性”提出較高要求。只要某標識是其創作人獨立完成,體現了作者獨特的設計和為此投入的智力勞動,就應判定為構成《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品”。就前述兩個案例而言,若僅就商標近似判定標準而言,前述圖十一與圖十二、圖十三與圖五應判定為構成相同或者近似商標,但是對其進行是否與他人“作品”構成“實質性相似”的判定時,因對于表現形式較為簡單的標識,對“實質性相似”的判定應以相同或幾乎完全相同為標準,在兩案標識圖樣存在一定差異的情況下,應判定為不構成“實質性相似”。由此可見,對“獨創性”不以達到“一定水準的智力創造高度”為要求,既符合《著作權法》鼓勵創作的立法本意,也不會使得“標志構成作品的在先商標獲得超越馳名商標的保護程度,破壞商標注冊及制度體系”。而且,在存在接觸過或接觸可能、且未經許可的情況下,將他人專為申請注冊商標而特別設計的、凝聚了他人智力成果的商標標識圖樣“原封不動”的用作自己商標注冊申請的圖樣,要么是覬覦該“作品”中的美感,要么是為了攀附他人商標商譽,要么是非以使用為目的的投機性、投資性搶注,該注冊行為本身是缺乏正當性的。對其予以有效制止,符合《商標法》維護誠實信用原則的立法精神和第三十二條“申請商標注冊不得損害他人現有的在先權利”規定的立法目的。
三、“在先著作權”的判定
由于作品創作私密性強、證據保留困難,作品創作時間及其著作權權屬的判定往往是評審案件中確認在先著作權的焦點與難點。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著作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七條規定:“當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權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權登記證書、認證機構出具的證明、取得權利的合同等,可以作為證據。”
實踐中,對于許多圖樣具有獨創性,構成《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品”的商標,其所有人創作該商標圖樣的主要目的就是用于商標使用,因此作品完成后,創作者一般不會、也很難對其進行除商標申請注冊、商標使用行為之外的“署名發表”,往往亦不會刻意對創作原稿進行保留。在無法提交創作原稿、委托創作協議或其他公開發表證據的情況下,當事人通常會提交著作權登記證書或者包含有爭議圖樣的在先商標注冊證以證明其對圖樣享有“在先著作權”。就著作權登記證書和在先商標注冊證在著作權歸屬判定中的證明效力,實踐中還存在著一定的爭議。
(一)著作權登記證書的證明效力
因著作權登記是各國著作權登記機關對作品著作權的歸屬予以初步確認,具有公信力與公示性,因此,著作權登記證書對在先著作權舉證具有重要意義,依據前述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著作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相關規定,它應是登記人對該登記作品享有著作權的初步證明。
實踐中,當事人為證明擁有在先著作權而提交的著作權登記證書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在系爭商標申請注冊日之前就已經在中國或其他《伯爾尼公約》成員國進行了登記的著作權登記證書(以下稱“在先著作權登記證書”);一類是在系爭商標申請注冊日之后在中國或其他《伯爾尼公約》成員國進行登記,但是其上記載作品創作完成日期早于系爭商標申請注冊日的著作權登記證書(以下稱“在后著作權登記證書”)。
對于在先著作權登記證書的證明效力,因其登記時間早于系爭商標注冊申請日,即使當事人僅僅提交了這一份證據,即使著作權登記證書中載明的作品創作時間系登記機構根據當事人的自述填寫,也可認為完成了享有“在先”著作權的初步舉證責任,舉證責任應轉移至對方當事人,如果其不能提供相反證據則可認定在“先著作權”成立。
而對于在后著作權登記證書的證明效力,由于我國和其他許多國家的著作權登記制度遵循自愿原則,著作權登記證書中載明的作品創作時間系登記機構根據當事人的自述填寫,登記機關并不進行實質審查,因此,如果當事人僅僅提交了一份在系爭商標申請注冊日之后登記的著作權登記證書,無法提供其他證據對作品創作時間予以佐證時,即使證書上記載的創作日期早于系爭商標的申請注冊日,也不足以證明他享有“在先”的著作權。此時,該當事人的初步舉證責任并未完成,舉證責任不發生轉移,對方當事人無需提供反證即可對其主張進行否定。
(二)在先商標注冊證的證明效力
我國《著作權法》第十一條第四款規定:“如無相反證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為作者。”也就是說,在無相反證據的情況下,可以推定在作品上署名的為作者。基于商標注冊的公示性,商評委曾在以往的部分案件中認為如果商標在先注冊,如無相反證據則商標注冊人可以推定為商標圖樣中獨創性作品的著作權人。法院在若干案件中,如第1207183號“上島及圖”商標爭議行政訴訟案[6]中,也曾認可了商評委的這種觀點。
但是,自2010年起法院開始在多件判決中認為僅憑在先商標注冊證不能證明在先著作權成立。例如第4539238號圖形(見圖十四)商標異議復審行政訴訟案中,北京市高院就在判決中明確表達了這種觀點[7],認為《著作權法》第十一條規定:“如無相反證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視為作者。”該條所指的“署名”是表明作者身份的署名,向公眾傳達的意思是署名者系作品創作者。商標公告、商標注冊證等商標注冊文件中載明的商標申請人及商標注冊人的信息僅僅表明商標申請權或注冊商標專用權的歸屬,其不屬于《著作權法》意義上在作品中表明作者身份的署名行為。因此,不能單獨依據NBA公司申請注冊相關注冊商標的行為直接認定NBA公司對芝加哥公牛隊隊徽或“公牛圖形”(見圖十五)享有在先著作權。
本文認為,從一般在先著作權的證明標準來看,僅憑在先商標注冊證是不能證明有關“在先著作權”的主張成立的。首先,從文件性質上來看,商標注冊證書是有關注冊商標專用權歸屬的證明,其上載明的注冊人向公眾傳達的是該商標的所有權主體的信息,而非《著作權法》意義上在作品中表明作者身份的署名行為。而且,實踐中,將已屬于公有領域的“作品”作為商標圖樣申請注冊商標的情況并不少見。商標注冊證書應該不屬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著作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七條規定中所指的“認證機構出具的證明”,僅憑在先商標注冊證不能證明該注冊商標的所有人是該商標圖樣的著作權人。
其次,著作權保護是有期限的。主張獲得在先著作權保護的權利人,除了需證明該作品的權利歸屬外,還必須證明該作品是尚處于著作權保護期限內的,而僅憑在先商標注冊證書是不能證明該商標圖樣作品的完成時間的,即不足以證明請求保護的作品尚處于著作權保護期內。
但如前所述,實踐中,許多商標圖樣作品的設計初衷即是作為商標使用,其著作權人可能除在先商標注冊證或者在后的著作權登記證書外,無法提交公開發表或者創作底稿等在著作權侵權民事案件中常見的證據。目前,有較大數量的涉及在先著作權保護案件中,一方面,權利人承擔著較重的舉證責任,而另一方面,“原封照搬”他人商標圖樣的當事人卻無需提供任何有關其獨立創作該圖樣或者對方當事人對該圖樣并不享有著作權等證據,許多在先商標圖案獨創性較強的權利人并不能獲得在先著作權的保護,這會使《商標法》中的“在先權利保護”條款無法正常發揮保護他人合法在先著作權,規制有違誠實信用原則的不當商標注冊行為的立法目的。
在前述第4539238號圖形商標異議復審行政訴訟案中,一方面,二審法院認為僅憑NBA公司在評審中提交的在先商標注冊證和相關在先行政裁定不足以證明其對“公牛圖形”享有在先著作權。另一方面,若允許該中國的自然人將眾所周知的美國全國籃球聯賽芝加哥公牛隊的隊徽作為商標注冊,則明顯與《商標法》中“在先權利保護”條款的立法目的相悖。二審法院以2001年《商標法》對異議主體和異議理由沒有限制的角度出發,認為“公牛圖形”是美國全國籃球聯賽芝加哥公牛隊的隊徽應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作為《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品,其著作權不可能歸屬于本案被異議商標的申請注冊人,從而判定被異議商標注冊人在未提交證據證明已獲得“公牛圖形”著作權人許可的情況下,將與眾所周知的美國全國籃球聯賽芝加哥公牛隊隊徽“公牛圖形”構成實質性相似的被異議商標標識作為商標加以申請注冊,會損害該作品作者享有的在先著作權。該裁定實際上回避了該“公牛圖形”是否尚處于著作權保護期限內的問題,實屬從《商標法》“在先權利保護”條款的立法目的出發,適當降低了對在先著作權的舉證要求。依據2013年《商標法》,依在先權利提出異議或者無效宣告的主體應為權利人或利害關系人,在此情況下,就無法再參照本案,回避在先商標注冊人是否是該圖樣的著作權人的問題了。
本文認為,要實現《商標法》“在先權利保護”條款的立法目的,并同時符合《著作權法》關于在先著作權的證明標準,關鍵在于應合理劃分此類案件中雙方當事人之間的舉證責任。一方面,若權利主張人僅僅提供了在先商標注冊證或者在后的著作權登記證書,則不能認為其完成了初步舉證責任,此時,舉證責任不應轉移至系爭商標所有人。另一方面,對于系爭商標圖樣與他人在先注冊商標圖樣完全相同或者構成實質性相似的,應充分考慮前述本條款的立法目的、權利主張人舉證困難的客觀情況以及雙方當事人權利爭議案件的民事屬性,采取優勢證據證明標準,合理確定舉證責任轉移節點,而不宜對權利主張人的證明標準設定過高要求。若權利主張人不僅提供了在先商標注冊證,還提供了在后的著作權登記證書、有關作品創作人的聲明、創作原稿、委托創作協議、有關著作權轉讓合同等證據中的一份或多份,應對在案證據予以綜合考量,只要能夠達到“合理相信的程度”,基本形成優勢證據,則舉證責任應轉移至系爭商標注冊人,由其承擔一定的舉證責任,提供相反證據證明在先商標權人并非商標圖樣的著作權權利人或者舉證其獨立完成創作了系爭商標圖樣等。如果不能提供證據或者證據不充分的,應當確認在先商標權人對該商標圖樣享有在先著作權。
四、“接觸可能”的判定
因著作權保護僅以該作品具有“獨創性”和“可復制性”為前提,所謂“獨創性”是強調獨立創作,而非抄襲、摹仿。客觀上可能存在均為作者獨立創作、但表達相似的作品,只要能夠證明二者均是獨立創作的,則均受到《著作權法》的平等保護。因此,與在商標惡意搶注判定中,商標獨創性強、兩商標高度近似就可以推定系爭商標注冊人具有主觀惡意不同,在先著作權的保護中“實質性相似”和“接觸可能”是兩個并列的要件,二者缺一不可,不能因圖樣間構成了“實質性相似”就推導出存在“接觸可能”,就是否存在“接觸可能”還需另行判定。
基于商標注冊的公示性,目前實踐中一般認為,若主張在先著作權的作品曾經作為在先注冊的商標圖樣予以注冊公示,則可以推定系爭商標注冊人具有“接觸可能”,而無論該在先注冊商標是在我國注冊,還是在外國注冊,亦或是國際注冊。例如,在第1962902號“獅城大藥房SHI CHENG DA YAO FANG及圖”(見圖十六)商標異議復審行政訴訟案[8]中,兩審法院均認為在被異議商標申請注冊日之前,含有上述作品的商標已在其他國家或地區獲準注冊并予以了公告,在無其他相反證據的情況下,可以合理的認定被異議商標申請人具有接觸涉案作品的可能性。
五、結語
本文認為,《商標法》中“申請商標注冊不得損害他人現有的在先權利”條款的立法目的并非要解決“權利沖突”,而是以保護他人其他合法在先權利為出發點,規制有違誠實信用原則的不當商標注冊行為。在適用本條款對在先著作權進行保護時,應回歸到“著作權保護”本身去確定證明標準,同時,在法律適用中應體現維護誠實信用原則、遏制惡意搶注的立法精神。
首先,應從“原創性”的角度上理解《著作權法實施條例》中的“獨創性”要求,不應對“獨創性”提出較高要求。只要某標識是其創作人獨立完成,體現了作者獨特的設計和為此投入的智力勞動,就應判定為構成《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品”。同時,應充分運用“實質性相似”這一要件對作品的保護范圍進行確定,對于表現形式較為簡單的作品,對實質性相似的判定要求較之構圖較為完整的美術作品,應更為嚴格。只有兩圖樣在線條設計或色彩、構圖上相同或者幾乎完全一致,抄襲明顯的情況下,才能獲得著作權的保護。
其次,要合理劃分涉及在先著作權保護案件中雙方當事人之間的舉證責任。一方面,若權利主張人僅僅提供了在先商標注冊證或者在后的著作權登記證書,則不能認為其完成了初步舉證責任。另一方面,對于系爭商標圖樣與他人在先注冊商標圖樣完全相同或者構成實質性相似的,要充分考慮前述本條款的立法目的、權利主張人舉證困難的客觀情況以及雙方當事人權利爭議案件的民事屬性,應采取優勢證據證明標準,對在案證據予以綜合考量,只要能夠達到“合理相信的程度”,則舉證責任應轉移至系爭商標注冊人,由其承擔一定的舉證責任,提供相反證據證明在先商標權人并非商標圖樣的著作權權利人或者舉證其獨立創作完成了系爭商標圖樣等。如果不能提供證據或者證據無法證明,應當確認在先商標權人對該商標圖樣享有在先著作權。
最后,在先著作權的保護案件中“實質性相似”和“接觸可能”是兩個并列的要件,二者缺一不可,就是否存在“接觸可能”需獨立進行判定。若主張在先著作權的作品曾經作為在先注冊的商標圖樣予以注冊公示,則可以推定系爭商標注冊人具有“接觸可能”。
參考文獻
[1]劉春田,知識產權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38。
[2]陳錦川,作品獨創性的司法判斷[J],人民司法,2008(9)。
[3]陳錦川,作品獨創性的司法判斷[J],人民司法,2008(9)。
[4]商評字【2012】第29064號裁定,(2012)一中知行初字第3157號判決,(2013)高行終字第728號判決。
[5]商評字【2011】第 30053號裁定,(2012)一中知行初字第732號判決,(2012)高行終字第1471號判決。
[6](2004)一中行初字第686號判決,(2005)高行終字第111號判決。
[7](2013)高行終字第343號判決。
[8](2010)一中知行初字第3223號判決,(2012)高行終字第595號判決。
文章標簽: 著作權
聲明:凡本網注明"來源:尚標商標轉讓平臺"或”來源:m.6zhiboba.com”的作品,均為本站原創,侵權必究!轉載請注明“來源:尚標”并標明本網網址m.6zhiboba.com!凡本網注明“來源:XXX(非尚標)”的作品,均轉載自其它媒體,轉載目的在于傳遞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網贊同其觀點和對其真實性負責。如因作品內容、版權和其它問題需要同本網聯系的,可撥打電話:400-7187-888。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