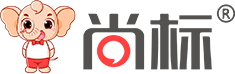如何理解“商標使用”在商標法和刑法中的“雙重標準”
來源:中華商標雜志 發布時間:2016-10-09 07:53:00 瀏覽:2915
隨著知識產權“三合一”審判實踐的不斷深入,人們開始發現,“商標使用”的概念在商標法和刑法語境中開始出現難以回避的沖突。
根據現行商標法第48條的規定,“本法所稱商標轉讓的使用,是指將商標用于商品、商品包裝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書上,或者將商標用于廣告宣傳、展覽以及其他商業活動中,用于識別商品來源的行為”。較之原商標法,新商標法對“商標使用”的內涵增加了“識別商品來源”的重要內容,體現出對商標核心功能的認識。按照這一精神,“商標使用”應當表明商品來源。“表明來源”要求商標的使用與特定的商品或服務相結合,同時使相關公眾得以通過該商標識別商品的來源。因此,那些不能表明商品來源的,不視為“商標使用”。例如,向公眾散發標有商標標識的廣告,但上面沒有注明商品及生廠商,就不構成“實際使用”。又如,僅僅制造他人注冊商標標識但尚未貼附于產品之上,由于沒有進入流通領域,公眾根本沒有機會看到,因此沒有起到“識別商品來源”的作用,同樣不應視為商標法上的“商標使用”。
然而,在刑法上,類似的在商標法上不被認為是“商標使用”的行為卻被納入犯罪。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7條進一步規定:“在計算制造、儲存、運輸和未銷售的假冒注冊商標侵權產品價值時,對于已經制作完成但尚未附著(含加貼)或者尚未全部附著(含加貼)假冒注冊商標標識的產品,如果有確實、充分證據證明該產品將假冒他人注冊商標,其價值計入非法經營數額。”根據上述意見,像“對于已經制作完成但尚未附著(含加貼)或者尚未全部附著(含加貼)假冒注冊商標標識的產品”之類沒有進入流通領域、商標標識尚未發揮商品來源識別作用的產品,也被認定到假冒注冊商標罪的非法經營數額中來。顯然,商標標識是否在商業流通領域中發揮來源識別作用,并不是假冒注冊商標罪所需要考慮的內容。
那么,應當如何理解這種刑法和商標法上的不同標準呢?答案仍然要從商標侵權與犯罪的標準上來看。
刑法第213條規定:“未經注冊商標所有人許可,在同一種商品上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的商標,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那么,什么是“情節特別嚴重呢”?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1條的規定,包括:非法經營數額在五萬元以上或者違法所得數額在三萬元以上的;假冒兩種以上注冊商標,非法經營數額在三萬元以上或者違法所得數額在二萬元以上的;有其他情節嚴重的情形。不難看出,對于假冒他人商標的行為,究竟是侵權還是犯罪,主要取決于“非法經營數額或者所得數額”,當“非法經營數額或者所得數額”達到司法解釋規定的標準時,就由侵權轉化為犯罪。
必須指出的是,盡管犯罪屬于性質嚴重的侵權行為,然而在假冒商標中卻出現了雙重標準:對于非法經營數額或者所得數額沒有達到犯罪標準的,“僅僅制造他人注冊商標標識但尚未貼附于產品之上”的行為由于沒有進入流通領域而混淆來源,并不必然構成商標侵權,嚴格來說甚至都不算“商標使用”;與之相對,一旦非法經營數額或者所得數額達到犯罪標準,這種連侵權都難以認定的行為卻被作為犯罪處理。這是為什么呢?
這是因為,在假冒注冊商標罪中,刑法的“防衛線”被前推了。從本質上來說,制造標識(但不貼附)和儲存假冒商標商品一樣,屬于假冒商標罪的預備行為或者準備行為。從刑法條文上來看,假冒注冊商標罪顯然應當屬于一種結果犯或者至少是行為犯,然而《解釋》將不對商標權人權益產生現實危險(未進入流通領域)的行為也納入犯罪考慮,顯然是將這種危害行為所產生的危險“抽象化”,使之具有危險犯的性質,換言之,將預防假冒商標犯罪的防衛線前推。這是因為,近年來我國大量發生的食品安全、質量事故、商標假冒等惡性刑事案件,使得人們開始正視一個事實:轉型時期的我國開始進入一個“風險社會”。伴隨著風險社會的來臨,結果本位主義的假冒商標刑法保護方式在預防“法律所不容許的危險”與法益保護方面日益顯得力不從心,假冒商標罪不但掠奪了權利人的經濟權益,而且造成大量的質量、食品、安全事故,給社會帶來極大的威脅,假冒注冊商標罪面臨著由罪責刑法向安全刑法的轉變,而司法解釋的上述規定,正體現了在這一背景下對假冒商標犯罪的日益增長的危害所作出的回應。因此,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知道“商標使用”在商標法和刑法中的雙重標準實質上就是“重其所重,輕其所輕”:對于僅僅構成侵權的,需要考慮是否真正進入流通領域產生現實損害;對于非法經營數額或者所得數額達到犯罪標準的,則要將行為人為實施犯罪的準備行為也納入到刑法的評價之中。
文章標簽: 商標法